【基礎科研】什麼是科學?
2014-10-16 17:55:00
原文网址:https://blog.udn.com/MengyuanWang/108908650
我這輩子做了兩個專業,第一個是高能物理,結果目睹了它被超弦這個偽科學取代的過程;後來改行做金融和經濟,結果發現美式的經濟學比超弦更離譜,完全成爲資本利益集團的宣傳部門。因此我對什麼是真科學、什麼是偽科學有些興趣。這個問題屬於哲學的範疇,做理工的一般不會接觸到;我當然也不是專家,這裡只是簡單地說說我所理解的資訊。如果解釋得不對,歡迎更正。
最常被引用,也是最古典的定義,是奧地利哲學家Karl Popper在1930年代所提出的。他認為科學是一個正式的邏輯系統(Interpreted Formal Logic),科學的發展過程就是不間斷地企圖來駁斥(Refute)這個系統的構件,所以真科學和偽科學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可以用實験駁斥的(也就是“證偽”,“Falsify”。請注意Popper的定義只說“證偽”而不是“證實”,因為再瘋狂的妄想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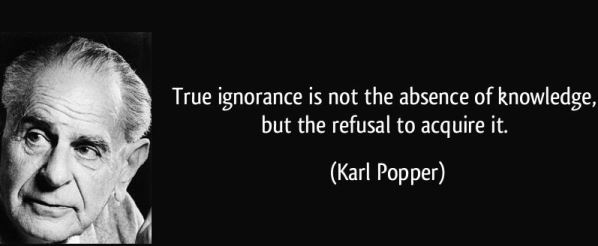
Karl Popper,二十世紀的知名哲學家和思想家;生於1902年,卒於1994年。學術生涯主要任教於英國首屈一指的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原本超弦早期(1980、1990年代)的問題在於它是建築在幾十個可能性無限小的假設上的,這些假設的真正辯護(Justification)是方便作者做計算,做了計算才能寫論文。我當時就覺得這些論文是為了出版而出版,它們是正確的可能性比那個作者當場被隕石打死的機會還要小很多;只不過那個可能性不是數學上的零,所以超弦雖然是糟糕的科學,還不能確定為淪落到偽科學的地步。等到Peter Woit開始寫他的部落格的時候,超弦界已經預測出10^500個不同的宇宙(10^500是多大的一個數字,一般人很難想像,讓我給幾個用來比較的例子吧。一個人的體重大約相當於10^28個氫原子,地球的質量大約比一個人大10^23倍,整個宇宙大約比地球重10^29倍,所以宇宙頂多只有10^80個原子。那麼超弦就當然不可能被任何實験來駁斥,於是Woit可以論斷超弦在Popper的定義下是一個典型的偽科學;做超弦的人也因此對Woit本人和Popper的定義恨之入骨。
其實哲學界自己對Popper的定義也有些意見:主要是Popper描述的是一個理想化的科學界;真實的世界裡,大部分的科學家還是把自己的論文當寳貝的。而科學的進步除了以實験來駁斥舊理論以外,發明新理論應該是一個至少同等重要的過程。因而在1950年代,美國哲學家Thomas Kuhn提出一個新的定義:科學是由互相競爭的理論體系(Paradigm)所構成,每個體係不斷地提出新的謎題(Puzzle),然後解答這些謎題。 Kuhn認為偽科學是提不出或解不出謎題的體系。
Kuhn的理論有很大的毛病:他的定義基本上描述的是所有現實中的學術研究機構。所謂的謎題和解答,定義很含糊,不只是科學和偽科學可以輕鬆地不斷提出謎題和解答,連明顯不是科學的學術科目也可以做得到。因此Kuhn的理論並沒有被哲學界廣泛接受,不過他至少啟發了匈牙利裔的哲學家Imre Lakatos的真偽分辨準據(Demarcation Criteria)。 Lakatos綜合了Popper的實験檢驗標準和Kuhn的新理論解答,而定義了所謂的進步學術(Progressive)和退步學術(Degenerative):能預測到出人意料的實験結果(Novel Facts)的叫進步,預測不出或者預測錯誤的叫退步。在互相競爭的理論體系中,最進步的是真科學,有點進步的是科學假設,完全退步的是偽科學。依照Lakatos的真偽分辨準據,超弦仍然是典型的偽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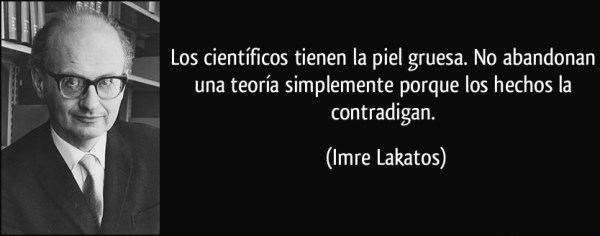
Imre Lakatos,數學家和哲學家。生於1922年,死於1974年;1960年起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得以與Karl Popper共事。本圖裡的西班牙文是這個意思:「科學家臉皮很厚,往往被現實證明是錯了之後還要耍賴」。用在做超弦的人身上,極為妥切。
那美式的經濟學算是什麼呢?美國的經濟學家不但不管事實結果,連理論的內容都處處違反邏輯。經濟學家的地位,不在於他的理論的實踐結果如何,也不在於他所做的假設和結論是否合理,而在於互相選美的知名度(Celebrity)競賽。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有時在同一年發給兩三個同一題材內的“大師”,而他們的理論卻南轅北轍、互相矛盾。這様的學術,連偽科學都談不上,純粹是宣傳洗腦的工具。
【後註一,2025/04/19】有朋友私下來信,針對最新的《龍行天下》節目(參見《美國的關稅、中國的冷靜,哪一個讓世界更震驚?》)做出批評質疑,我覺得值得作爲這篇正文的參照,所以將問答轉列於下。
<問>說到想早上節目是因為怕說晚了就沒法展現先見之明時(知道您是戲言)覺得真挺失望的,尤其是之後又反复提及如何提前預判什麼什麼事,外人看到難免會想“這就是他的追求?格局也太小了吧?”
<答>我反復强調自己的預測正確,並不是出於傲慢或虛榮,其實是很早以前就在深思熟慮之後定下方針、有意地試圖扭轉文化。你所説的“格局”,本質是拿空洞的内涵來裝逼(亦即“大師風範”);這的確是一門大本事,是在商場和學界勝出的關鍵,但問題在於治國不能這樣搞,否則普選制挑選出來的“人才”,例如Obama這種口若懸河的人,就會是最優的了。別忘了,博客討論的議題,一進一出動輒幾萬億美元,任何犧牲精確度和完整性的婉轉,都是我的良心不容許加諸於國家的潛在損失。
博客的最核心論述,就是治國(亦即博文常説的“管理公共事務”)必須依憑科學理性。什麽是科學的好壞標準?不是看聽衆喜不喜歡,不是看大佬點不點頭,不是看裝逼高不高檔,不是看論文登上哪個期刊,而是要看預測是否兌現(博客不是常説,“事實”比“邏輯”還要優先?檢討預測是否兌現,就是“事實”和“邏輯”的碰撞過程),而且越是事先被主流排斥、事後卻被證實的,越是重要、正確和難得。這個標準對自然科學出身的人,都已成爲本能,但社會科學也絕對應該如此,偏偏當代的社科界完全沒有這個概念,這也正是世界上這麽多政壇的所謂精英卻在政策上極端幼稚的根本源頭。
博客的大目標是爲國建言,主要手段則是通過優質的内容和態度來提升輿論水平,那麽以身作則、倒逼社科學界檢討自己的預測是否正確,不正是最關鍵的文化任務之一嗎?你看十幾年前的網紅學者,全都爲了裝逼、維持你所説的“格局”,從來沒有人會檢驗自己的預測,反正都是錯的;但是今年Trump當選後,就有不止一個知名大佬站出來說我們四年前就預言Trump會“捲土重來”。雖然他們是在狡辯作弊(因爲四年前他們預測的,不是Trump會在2024年當選,而是會試圖重新出來競選的廢話,也就是利用了中文裏“捲土重來”的語義含糊性),卻讓我很高興:中國社科界終於開始接受科學標準了,這是博客11年努力的又一成果。
【後註二,2025/05/19】我終於在本月的《龍行天下》節目(參見《從「印巴空戰」看世界真正危機!》)中找到機會討論科學方法論,不過因時長和格式所限,講得非常淺顯簡略,讀者還是必須回到博客來尋找完整而精確的論述,並且基本的邏輯學和統計學知識也是必要的。例如節目中提到,若是事前判斷開大的機率為90%,那麽預測者依然必須100%猜大,事後的成功率也只能達到90%。這裏我的用意主要在於示範最佳策略對博弈條件的非綫性反應,稍稍觸及綫性思維的局限性;然而有公衆評論,把這稱爲10%失誤的托詞,這顯然是對統計學完全無知的誤解:博客反復解釋過(參見《讀者須知》和其下的留言討論),我做預測的標準門檻是90%,事後的成功率也至少是90%,然而統計學的基本常識之一是誤差以平方和叠加,所以事後的誤差是事前誤差與我判斷誤差的平方和再開平方根,既然事前、事後的誤差基本相等,就代表著博客分析失誤所引發的誤差可忽略,亦即至少低半個數量級;換句話說,分析錯誤的比率其實是在3%以下,以往只不過不想表彰自我、於是懶得花時間討論數學細節,畢竟10%的總誤差已經比他人強了兩個數量級,足以證明科學分析的優越性。但愚民反而做出與事實相反的結論,不但抹黑其為托詞,還有把科學預測的例常印證檢討硬説成自誇的,這其實正反映了當代公共論壇的墮落機制:習慣謊言和蠢話之後,連最基本的隨機中性反應(亦即正反機率相等、信息量爲零的亂猜,華爾街笑稱為“扔飛鏢的猴子”)都做不到,而是會對真相和誠實產生主觀反感,自動選擇虛僞愚昧,體現了“人性本蠢”並非虛言。
13 条留言
王博士最近的回复里多次提到第一原则。这个词我不太懂,去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它近似于欧氏几何里的公理。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概念:首先,如果定义了一些公理,那么如何保证公理是正确的呢?比如美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就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其次,我不太明白日常生活中怎么应用第一原则。我的理解是先确定基本事实(相当于证明题中的初始条件),再从事实出发利用规律(相当于数学中的公理、定理等)逐步推导结论。请问这种推导结论的过程是否符合第一原则?
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个方法论问题。王博士批评的简单类比思维,其本质就是归纳法。归纳法是不安全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猪圈里的猪认为打铃是天降饲料的原因,直到某天屠夫来临”。社科领域问题极为复杂,难以通过实验复现来检验,只能通过历史记录寻找规律。这一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归纳法(虽然同行之间可以交流,但大家本质还是在用归纳法,顶多只能在基本事实上互通有无),得出规律的可靠性自然要打问号(比如国内流行的“因为自由民主,所以国富民安”观点,就是典型的归纳法结论)。既然规律可靠性要打问号,那么第一段中描述的推导过程也很可能不可靠。那到底该怎么得到可靠的社科判断呢?
PS:我搜索第一原则的解释时,发现它在物理学中有许多应用,但我的物理水平只是用课本里的物理规律解题而已,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原则的应用。
在自然科學裏,若是把假設拿來冒充為已確定事實,層層堆砌,像是超弦,就自然演變成爲僞科學。在社科上,因爲美宣對維持霸權有重要作用,這樣的冒充頂替更是有長久的歷史和充分的資源,被系統化和普世化了。例如美國人假裝直選制是普世價值,就不是第一原則;如果貿然接受作爲前提,後續討論就毫無意義。我從演化論去討論真正普世價值的特性,才是從第一原則出發。
“從演化論去討論真正普世價值的特性”,我在過去兩個月就提過兩次。留言回復你不用心讀,只管發自己的問題,嚴重違反博客規則,那則留言被刪了,禁言一個月。
信息论的一个结论是:输入信号无损压缩后的大小不能低于熵值。这是不考虑数据特征,仅依赖概率论推导而来。如果考虑了特征,该大小可以进一步降低,比如运用压缩感知技术(近似无损);特别情况下,由算法生成的数据,其信息压缩效率可以非常高(kolmogorov 复杂度)。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本身是由一个个信息压缩机器构成的系统。以基础科研为例,研究人员在主观选定研究主题和探索方向后,日常工作就是研究如何更精简地表征研究数据(无损压缩)。研究过程会经历反复试错,最后的结晶就是逻辑框架(一将功成万骨枯)。话句话说,逻辑框架是输入数据在特定视角下的无损压缩算法(实际是近似无损),是主观视角和客观逻辑矛盾结合的产物。数学的逻辑框架是公理体系,由定义、公理和定理组成;物理的逻辑框架是定律和方程,定律由实验总结而来,方程依赖严格的数学推导。
主观视角是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突破被熵锁死的容量下限。回顾历史,近代数学和物理学上的革命,都来源于观念上的进步,用更高的观点、更精简的语言来解释更广泛的现象。但要注意,对现象的解释只是理解现象的一种视角,即使这种视角非常强大,却不等同于现象本身。与其说“大道至简”,不如说人只能理解简单的道,太复杂的问题就难以说出因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人力有时而穷,科学的进步是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得来的。
客观逻辑也是必要条件。即便一个人对孤立事件的直觉很对,成功率达到九成,那么他连续拍四次脑袋做成一件事的概率,就迅速衰减到六成,信息率接近零。所以对复杂问题直接丢出结论是无意义的。结构化的逻辑推理构成逻辑框架。只有借助逻辑框架,从现象到结论过程中的信息损耗才能尽力降到最低,才能保证预测的品质。逻辑框架还能简化问题,便于看清主线、忽略旁支、消除噪音。实际研究中,往现有框架上再叠加一层,就是很好的进展;如果能直接精简框架,那就是大突破。物理学自伽利略开始几百年来叠床架屋,却又踏实稳固、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体系一直在革新,维持逻辑框架的品质。
除了压缩,信息论的另一个主题是信道。语言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信道。科学语言是其中特别的一支——低容量、高带宽;伪科学可以当成信道中的噪声,噪声太高会干扰信号传输速率(浪费资源在纠错上),甚至误导结果。我感觉,古代中国没有发明精准传递思想的第二语言(比如数学语言),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从历史案例中悟道太吃天赋了,哲学思辨也不利于实操,导致古人的智慧、经验和教训难以随时空稳定传递给后人。
昨天我看到Sabine的新視頻《Atomic Anomaly Confirmed! Evidence for a “dark force”?》,有些感慨:物理學竟然已經墮落到與你所述的抽象理想背道而馳的地步。這裏她討論一個MIT團隊在2020年所發表的研究結果,今年又增進了測量精度,開始宣稱“違反標準模型達23個σ”;偏偏她只是照本宣科復述了那篇論文的Abstract提要,連到底什麽東西去違反了標準模型都語焉不詳,讓我非常失望。還好我是極少數有能力去理解原始論文的人之一,所以花時間搜索並閲讀之後,原來他們鑽研的是所謂的King Plot of Isotope Shifts,也就是找幾個同位素,然後測量特定的電子能階,畫出其與原子核質量的關係;這在理論上應該是綫性的,但他們發現了非綫性關係,偏離平均綫達到23個σ。以上沒有什麽毛病,問題出在“違反標準模型”那句話;這是因爲算出應該是綫性關係的理論有好幾層,標準模型只是最底層的基礎,上面還有一大堆包含著各式各樣簡化假設的其他理論,例如同位素原子核大小和形狀可能隨中子數目增加而有非綫性變化就被忽略無視了。用一般人也可以理解的比喻來説,就像是三更半夜窗簾忽然明亮起來,測量有光照達到23個σ的確定性,然後MIT這群人就驚呼“23個σ保證太陽在半夜升起”,無視人爲探照燈照射窗戶的可能性。這裏的根本問題在於科研界的獎勵機制,是“太陽在半夜升起”論文才有期刊願意登,說探照燈根本沒人理你;而網紅如Sabine的邏輯,也同樣是“太陽在半夜升起”才足夠吸睛,而能拒絕金錢誘惑、堅持當義工推廣真相的,又有多少人呢?
回到前面所提的,一切學術題材都有人治主觀因素,包括科研在内。很不幸的,自由市場在初期提升效率之外,還有導致壟斷、金融化、和浮誇/粗鄙化("Race to the bottom" effect;這是經濟學效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搜索Wikipedia)的强烈副作用,金融化更會加速後者。這裏的根本癥結,在於高能理論物理學徹底脫離實驗檢驗的範疇,不再如工程項目那樣可以簡單由成果倒推好壞;這其實是基礎科研的通病,也是爲什麽我反復强調管理基礎科研和管理產業研發,適用的原則剛好相反。你這次所提的,理想中科研進步的抽象描述,偏向基礎理論,所以必須特別小心被人性和管理機制所扭曲。
我同时也意识到,对自然科学的 Meta 论述是自然科学知识集合的子集,所以认识不论多么深刻,一定是局限的、不完备的,应用时必须考虑适用范围,生搬硬套既有结论只是贻笑大方。不过一旦找到了合适的视角,结论就如泉涌。比如 Kelly 公式告诉我们最理性的下注比例应该是真实风险比例,所以很自然,管理极低成功概率的基础科研,就不能孤注一掷,不然“赌”不了几局,本就输光了;而人为扭曲赔率,目的正是希望对手接盘,自己反向操作套利。
博客对我在思考社科问题上也有启发。人对社会的改造越深化(当前是信息化),人性就越是影响社会演进的方向。自上而下,政治家的主观偏好影响全球格局;自下而上,群体团结可以激发伟力,而 Herd Mentality 则自我伤害。社会存在大大小小的内生周期性波动,人性很可能是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验证这个猜想,需要积累阅历。
幾個月前我曾突發奇想,考慮建議中國官方主辦一個社科預測競賽榜,持續以實際勝率來分辨每個教授和研究員的水分,那麽理論上社科界的人員選拔將比自然科學界的唯論文之上論還要精準;但立刻想到出題本身對認知和品格的要求都極高,我所知的大陸無人能做到。例如題目必須專注在可約的不確定性維度,否則對錯都是隨機的,毫無意義;而分辨可約和不可約不確定性,除了我之外,你還看到誰討論過?連概念都沒有,怎麽精確執行?十年前美國學界曾自己辦了一個類似的競賽,很快無疾而終;除了題目水準糟糕之外,另一個因素是少數那些較好的題目,都是民間不知名人士勝出,讓學術人臉上無光。打臉行内既得利益的體系設計,交由官僚或學術界自理的結果,就是必然扭曲規則、大開後門造成各種隱性的作弊,所以這個主意也就被我自己的反省過濾掉了。
看了樓下社科預測競賽榜的分析,那不是是代表統治階級不管官僚或是資本家要出現非平庸的人制定政策機率都很低,我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只是統治階級"偶然"出現一個非平庸又兼具品質無私的人機率偏低,既然如此非平庸的頂尖聰明的人出現在非統治階級的機率是不是高於那一小群既得利益者,畢竟統治階級人口基數少又很有大概率代代世襲,因為自私的人類的數量多過無私的人類數量只能用概率來預測,那麼底層人口基數大聰明又兼具品德的人是否在底層的總數就大於上層而又無法掌握權力,而頂層菁英或許有後天家庭教育的優勢,但先天的智商容易均值回歸到普通人身上(後天軟體在強硬體不行也沒用),就算開國或是創業家偶然有出類拔萃之人,世襲個兩三代也必定均值回歸,因為誰也不知道下一代世襲權力的人不論官僚或資本家會是什麼特性的人,返回平庸才是統計的大機率事件
畢竟連學術界和科學體系裡的判官和權威也會腐化,人類的歷史必然就是輪迴的就像改朝換代一樣的結構性的惡性循環,不是有句名言:「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 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汲取任何教訓」
不過你的結論因而被進一步加强了:和平穩定狀態下,任何人類群體的自我腐化動力都極為强烈,這不但是朝代周期率的由來,映射在市場經濟上,也引發了Pic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中所討論的財富集中效應。
即便是忽略隨機性、只考慮因果效應,最能穩定產生正面回報的,也不是才能或貢獻,而是掠奪,參考白人通過殖民而主宰世界500年的歷史。要排除掠奪,就必須有强大、詳細、合理並與時俱進的公共規則,但誰來主持、設計和管理這些規則呢?理想中是兼具智慧、品德和熱忱的賢能者,但現實與理想距離甚遠,實際上是比爛的世界,中國只不過是當前最不低效腐敗的體系罷了,這還是十幾年前運氣爆棚、有習近平這樣改革者上位的結果。
我所構想的社科預測競賽榜其實也有成功的可能,只不過需要足夠的資源和聚焦,把規模和熱度提升超過臨界點,就可以藉助公衆的關注來維持公平性;然而這似乎不是我一個人呼籲所能做到的。
国际社会去年发生很多“黑天鹅”事件,战略学界对这些主要发生在欧美的事件大多没预测对。不仅中国学界如此,欧美学界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中国战略学界的失误是欧美学界预测不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处在北京,对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进行预判时要参考欧美同行的研究。欧美战略学界预测失误,直接导致世界性的预测失误。
社会天然有着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对这类重大国际事件,希望学界能够作出正确预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学者也有这种抱负,希望在预测方面有所成就。只是社会科学本身就有落后性,学科成熟度低,主要功能是在事件发生后进行“马后炮”的解释,但预测功能确实很弱。
我们只能根据同类事件过去出现的多次博弈和经验,进行一些有关事态会否发生以及在何等形势下发生的判断,但不可能“后知五百载”。现在人们指责战略学界对去年这些重大国际性事态预测失误,但按照严格科学的预测标准,对20年前苏联解体那种量级的事件,也是没任何学者真正预测到的。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
以及2019年金灿荣在香港一场讲座上的部分发言:“(关于英国脱欧)当时我们国内很多智库都要递报告,我也递了。我后来了解,好像全国几十份报告全部都错了,最后就脱(欧)了。后来好像领导人还挺恼火的,给你们这么多钱,养这么多人,你一个都不对呢,全错了。好到了年底吧,不是美国大选嘛,希拉里、特朗普对吧? 到年底中央又要我们递报告,我们学精了,每个单位准备两份报告,而且都准备出结果来交,说全对了。但是还是挨了骂,因为人家要你预测,全部都是事后诸葛亮”。
以上内容供王老师参考,对于中国社科界对此问题的态度可见一斑。
建立認識框架艱難的一大問題在於不像自然科學方面重複實驗和觀測可以不斷校驗一個理論,而世事的觀測重複遠不如實驗那樣便捷,同時真實觀測結果經常會被人為掩蓋甚至修改欺詐,新聞報告也不存在科學期刊peer review這種校正程序,這些都使得準確的對世事認識框架難以快速建立。
對於尋求真實我個人有異乎尋常的激情(passion),我曾認真思考如何建立個website幫助人們梳理真實與謊言,但發現即使在AI躍遷的今天仍然是個labor intensive的工作,而一旦labor intensive就不可避免地傾向主觀,無法客觀的website接受度就存疑。儘管技術上有局限我仍然長時間相信給信息源評估信用這件事的意義重大,然而現實告訴,像Ground News那樣給信息標識左右在我看來根本在浪費資源,但是讓我痛苦的問題在於絕大多數人似乎對追求真相這事兒並不在意,倒是了解左右立場更引人注意。我曾以為世人都關心真實的世事,不過現實不斷教訓我:世人都關心符合其三觀的敘事(narrative),與事實無關!
舉例來說,我看到最近Trump與哈佛大學的戰鬥至少有三種敘事(narratives):1)左翼民主黨將其描繪成專制Trump對思想教育自由挑戰和霸凌;2)而pro Trump的則稱其為Trump對deep state抗爭的延展,是對建制派白手套的精準打擊,比如美國務院前官員Mike Benz報告說哈佛是USAID、國務院、CIA在教育界的影子;3)也有人稱是Trump利用院外猶太集團對院校反猶活動動用政治資源的機會試圖改變美國大學嚴重白左的傾向。哪個敘事接近真相,或者都是真相的一部分,陷身於實時變化的信息迷霧中我們無從得知。如果有讓人信服的認識框架給普通大眾更接近真實的認知解讀對所有人都將是幸福之舉:敘事1的信用是幾、敘事2的信用多少等等。
我討論建構認知架構的用意,在於示範思維模式和辯證規則。以我自己的經驗,在高中一看到“黨外”(80年代的臺獨勢力)宣傳的時候,就立刻知道它邏輯上不靠譜,因爲這些人的基本敘事出發點就是錯的(亦即他們說(1)貪腐來自“獨裁”;可貪腐明明是普世人性,不同政治體系下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出來,只看以吃拿卡要為形式的貪腐才是“集權”式政體的特徵;(2)台灣獨立是國族認同問題;實際上國族認同是想不想要的問題,的確應該以多數決,但公共議題、尤其是基本政體,當然應該先問可不可能和應不應該,兩者都過了,才是想不想要的問題)。然而光是這樣的天生邏輯洞察力依舊遠遠不足以立即自建認知架構(所以當時也盡量避免公開爭辯這些話題),又經過30多年的學術和金融經歷,無數的論文閲讀和自我辯證之後,參照或批判了許多前人的分析見解,才有能力寫博客。對比現代網絡噴子,連中學級別的思維能力都沒有,更別提正確的認知架構,偏偏他們發言聲量最大;讀者求真的第一步,應該是養成自我檢討反省的習慣,避免談論未100%確認的論點,而不是奢求自建認知架構。
其次,對正確的認知架構,重要的恰恰不是自主建立,而是能拿來應用、過濾假説,並且在被糾正後願意接受。例如醫學其實是生物學的應用分支之一,而生物學的基本認知模型就是演化論,所以任何醫學上的敘事都必須先通過與演化論邏輯自洽的過濾,這也正是中醫教徒反科學、反理性的基本表徵之一:中醫教所吹捧的“藥品”大多和演化論格格不入(讀者可以拿冬蟲夏草為案例來自我辯證,並參考《一個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後註十五】),應該在第一秒鐘就被扔到垃圾桶,但他們幾千萬人、幾十年下來,連一個討論辯解都沒有,可見其愚蠢程度之離譜。這裏讀者應該學習的要點,在於檢討面臨認知挑戰的時候,直覺反應是不是直面證據的真實性;如果腦子自動跳到《常見的狡辯術》,或者乾脆回避反面證據,自説自話,重複己方已被反駁的論據(這是中醫教的通病,我至今還沒有看到敢正面回應安慰劑效應和雙盲實驗的),那麽你已經得了印度病,這是不治之症,再怎麽多讀博客也不會有療效。
至於你所提Trump vs Harvard的三個解釋,除了第一個是明顯謬誤的詆毀之外,後面兩項都是片面正確的描述。這裏你對“認知架構”顯然有相當誤解:認知架構是大框架的基本理論模型,對特定細節可以做出詮釋,也就是討論低一個層級的“事件本質”,但這個“事件本質”當然不一定是單一的;例如在你所舉的案例裏,不同的參與者即便暫時結盟,也可以有不同的動機。而這個事件上層的認知架構,則是“500年白人殖民體系的第三代:美國金融殖民帝國的腐敗”這樣的大模型,哪有什麽疑義?
要推進對世界認知模型的框架和假設還有一個更省力的方法,一開始就耗費大量時間尋找證據當然比較費力,因此第一關應該是邏輯要自洽無矛盾,如果連第一關的考驗都通不過的認知模型就沒必要繼續浪費資源完善可以直接放棄,第一關就是尋找既有主流的認知和模型裡的邏輯無法自洽的缺陷,然後建立另一個平行的假設版本與之競爭在比較看看哪個模型的邏輯無法自洽無法自圓其說缺陷更多,最後優勝劣汰再讓剩下來的假設和模型去找現實世界裡的證據這樣就足以過濾掉99%以上的無法自圓其說的認知模型或是需要依賴太多前提條件而別人用更少條件更簡單就能解釋與事實不矛盾的的認知框架(也就是奧卡姆剃刀原理)除非有發現更多證據去支持更複雜的假設
比如樓下說的那三個敘事如果連什麼是專制都沒有準確定義就無法進行理論推導更無法有效論證,比如美國常常把一些跟自己理念不符的但一樣透過西方民主程序選出來的國家的總統也認定成是專制國家比如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但卻忽略自己一樣是受財團和利益集團操控選舉然後直接給人貼標籤說是不民主,第二點是民主未必高效率也不一定做正確決策因為人類智商分佈是大多數人並不聰明且大多數人自私所以蠢人也可能做損人不利己的決策,即使理性的人也可能做損人利己的自私決策,因此世界上並無完美的制度都受到人性自身缺陷的影響
因此我認為人性每個個體如果有兩大獨立的變數愚蠢和自私程度,統計上來講愚蠢的人較聰明的人多,自私的人較無私的人多,並且假設自私的人會把權力或財富傳給下一代那麼就可以推論體制的優缺點,如果把西方的那種民主定義成有多少人掌控政治權力那西方的民主至少在古代一路是由希臘羅馬那種只有貴族和奴隸主才有的選舉權演變而來,只是典型的寡頭政治到現在都沒有打破這一點只是改由財團治國是依靠世襲財富來繼承權利底下的古典時代的奴隸、中世紀的農奴或現代勞工都沒有實際掌握權力
古代東亞國家比較接近中央集權統治人數較少效率更高但傳統上是依靠世襲權力,儘管中國古代有一種偉大的創新就是科舉制度可以通過考試把底層的聰明人拉上士大夫和統治階級官僚一開始成效也不錯,幾百年後制度也可能被癱瘓最後變成有錢子弟才能讀的起書世襲當官
最優秀的體制應該是可以讓最優秀的人獲得權力而限制世襲或繼承權力,因為底層的人口總數較多因此有較大概率產生較多的聰明人,例如假設先天智商高於一定程度標準的人從遺傳的觀點來看底層和上層一樣機率例如都是1%或0.01%是相對少數(具體數字不是重點重點在認知模型)那頂層的人口總數如果是100萬人就有1%也就是1萬個聰明人適合當管理,底層人口是80億人如果也是1%那就有8000萬個聰明人但是很明顯因為家庭教育和社會資源的分配因此上層階級後代很明顯會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更早認知社會,而底層的聰明人認知比上層晚10年這就很晚了影響生涯發展
而遺傳這種東西又很隨機的至少很難掌握其中規律,因此不聰明的人也可能生下聰明的後代(隱性基因隔代遺傳),相反聰明的父母後代也可能均值回歸,而自私的人數量較多這又會導致頂層的100萬人當中的大部分人會把權力世襲給後代,極少人傳賢不傳子,而底層的聰明人會受到國家機器的壓制,這是人類改朝換代惡性循環的機制,因為沒有保障的機制總是能讓聰明的人獲得權力(科舉制度是一個創舉在一小短時間裡打破這種惡性循環),論證:舉例來說在貧民窟長大的高智商兒童並不比平庸的統治者後代有更大機會獲得上升通道
至於選賢與能的重要性,博客已經反復强調過多次,所以科舉制的正面價值遠高於其副作用。當代中國的人材選拔問題,除了一大堆迷信白左歪論的官員學者引入越改越爛的“改革”之外,還有40年改開的迅速致富經驗所引發的功利心態,非常不利於培養公益爲上的士大夫精神,反而學術人都急於拿聲譽和人品來換取現金,例如丘成桐。
選拔公共服務官員好壞的本質首先不在於是否找到了聰明人,而必須是找到願意將大眾利益放在個人之上的人,這是非常困難的任務,而西方全民選舉系統用幾十年給我們證明了他們無法有效完成這個任務。是否有公心和是否有能力,在公共服務領域無容置疑選拔公心是最重要的一環。孔夫子春秋時代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但是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也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的實現和執行幾乎是不可能任務,一百多年前中國精英們集體幾乎否定了儒家給出的答案。但我相信要不是中國有一代代以公心為民付出的精英,根本沒可能用一百多年時間追平與西方的競爭。
我覺得執掌權力影響政局的人都是聰明人這樣的假設和觀察到的事實不符,會有這個思想誤區是因為忽略了權力可以世襲到不怎麼聰明的後代,也忽略的底層的人口基數的大數統計,再透過國家機器運作的僵固性、慣性和體制創立之後持久性來維持開國君主或創業家後代100~200年的統治,即使他們不比開國和創業者的前輩優秀一樣能維持統治,因為國家機器和隱性遊戲規則的存在底層階級上升通道會受到壓制,不論西方那種寡頭政治用金錢來延續統治階級的權力,或者亞洲國家用政權來延續都是可以繼承的,如果不是這樣假設,豈不是要假設統治階級後代有更高機率生出先天智商更高的後代(但這種假設不合邏輯)因為這樣假設違反生物遺傳學原理,歐洲上層階級為什麼歐洲古代貴族政治聯姻「近親繁殖通婚」那麼久也沒有出現人類的品種改良出現不同的人類品種或智商特別高的後代? 這樣的假設邏輯無法自洽也無法自圓其說
東方國家舉例:慈禧太后、晉惠帝(何不食肉糜)都沒有做出正確決策來對國家也好對自己個人利益也好,甚至以個人利益的角度來思考也不是最優解是損人不利己的,但越接近開國創業那一代清朝的康熙、唐太宗的這類治理水平明顯就比這些後代高很多
西方國家舉例:富二代繼承財富來維持權力也可以維持上百年比如歐洲的老貴族
王老师您好,诸如“演化论、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公益最大化、道德规范的根本目的是公益最大化,阴谋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动机+能力+证据、还有您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等”都属于第一原则,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